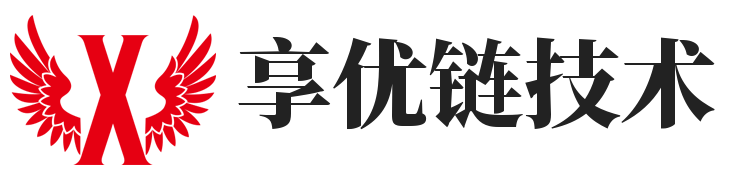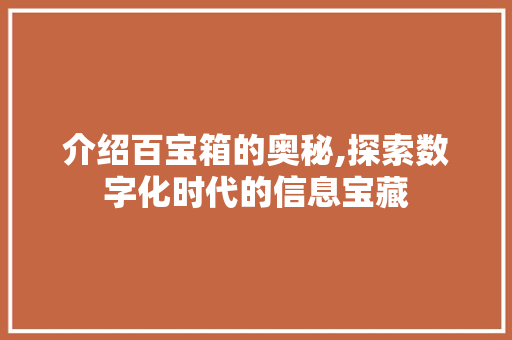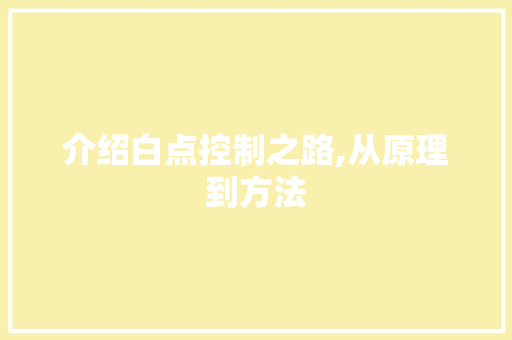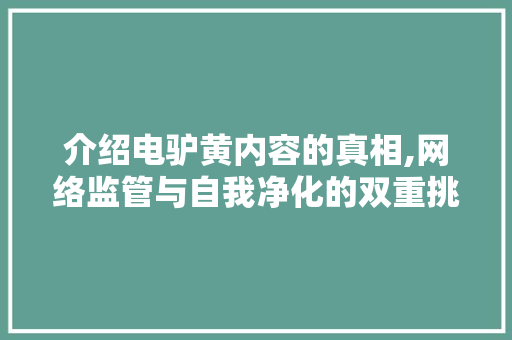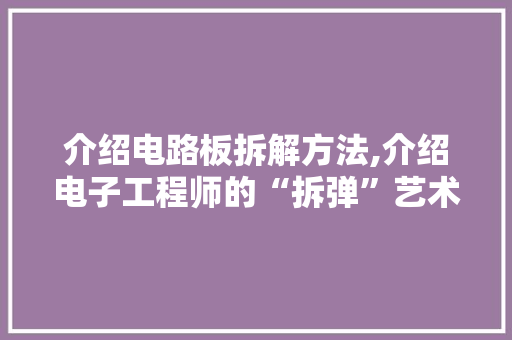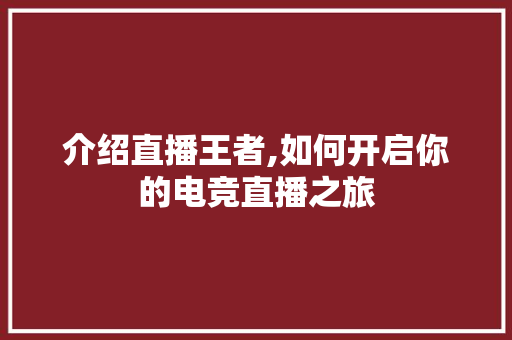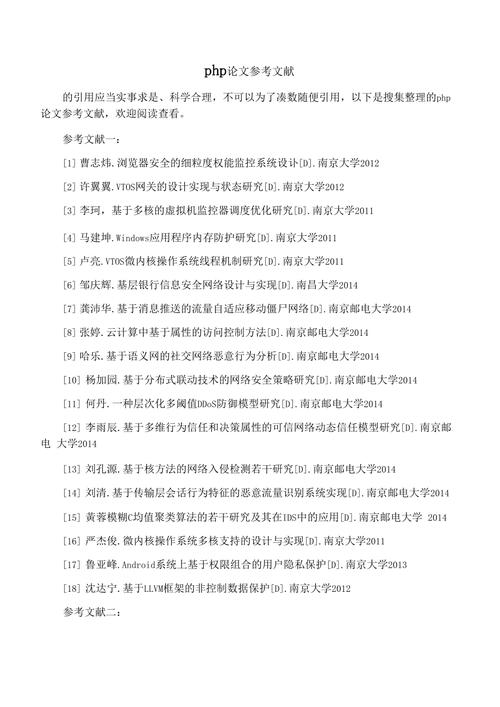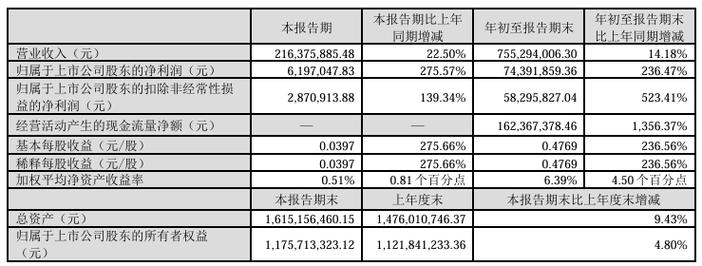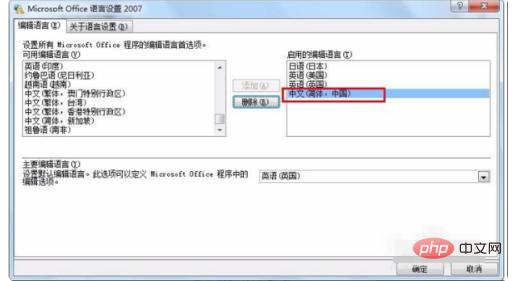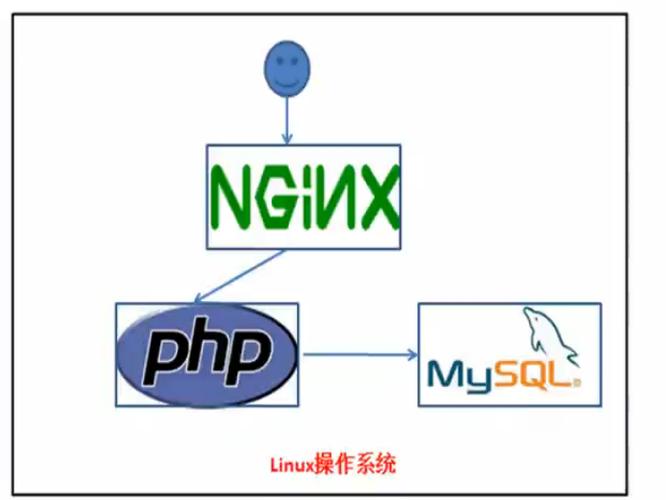本雅明
译者的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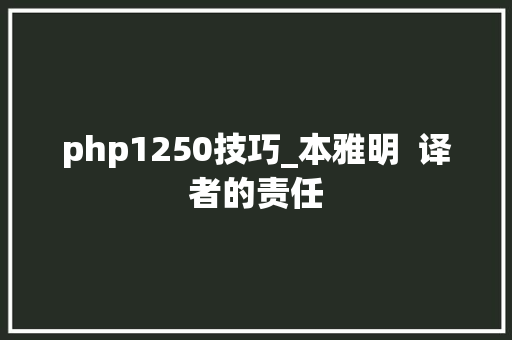
作者:瓦尔特·本雅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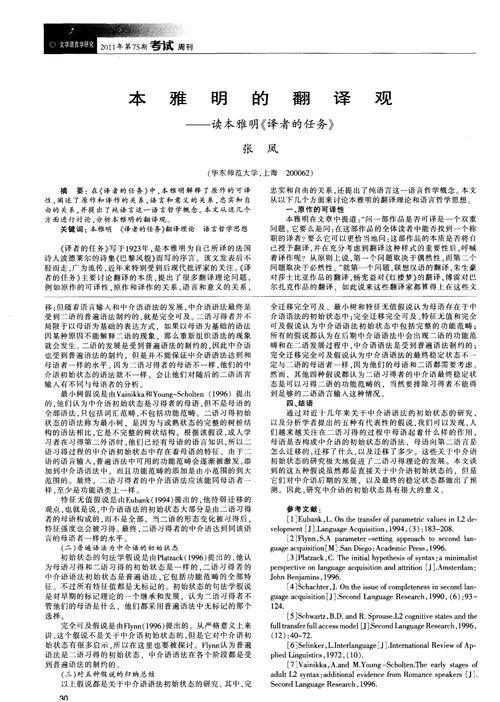
译者:张旭东
转自:人文与社会(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1250)
在欣赏艺术作品或艺术形式的过程中,不雅观赏者的成分从未带给人什么收成。评论辩论什么"大众年夜众或其代表人物在此只能使人误入歧途,乃至连“空想的”接管者这个观点在磋商艺术时也有害无益,由于它无非是设定了自身的实质和在场性。艺术以同样的办法设定了人的肉体和精神的存在,然而艺术作品却从未关注过人对它的回应。从来没有哪一首诗是为它的读者而作的,从来没有哪一幅画是为不雅观赏家而画的,也从没有哪首交响乐是为听众而谱写的。
那么译作是为不懂原作的人准备的么?如果是的话,这倒是以解释在艺术领域里不谙原作的读者有多么广大了。再说,这彷佛也是把 “同样的话”再说一遍唯一可以想见的情由。可是一部文学作品到底“说”了什么?它在同我们互换什么呢?对那些领会了作品的人,它险些什么也没“见告”他们。文学作品的基本特性并不是陈述事实或发布信息。然而任何实行传播功能的翻译所传播的只能是信息,也便是说,它传播的只是非实质的东西。这是拙劣译文的特色。但是人们普遍认为为文学作品的本色是信息之外的东西。就连拙劣的译者也承认,文学作品的精髓是某种深不可测的、神秘的、“诗意的”东西;翻译家如要再现这种东西,自己必须也是一个墨客。事实上,这带来了劣质翻译的另一特点,我们不妨称之为不准确地翻译非实质内容。只要译作迎合读者,这种情形就会发生。实在假如原作是为读者而写的话,它也会陷入同样的田地。可是,如果原作者并不为读者而存在,我们又若何来理解不为读者而存在的译作呢?
翻译是一种样式。把它理解为样式,人们就得返诸原作,由于这包含了支配翻译的法则:可译性。问一部作品是否可译是一个双重问题。它要么是问:在这部作品的全体读者中能不能找到一个称职的译者?要么它可以更恰当地问:这部作品的实质是否将自己付与翻译,并在充分考虑到翻译这种样式的主要性之后,呼喊着译作呢?从原则上讲,第一个问题取决于有时性,而第二个问题取决于一定性。只有肤浅的头脑才会否认第二个问题的独立性,才会把两个问题看得同样主要。我们应该指出,某些干系的观点只有当同人联系起来时才故意义,有时或许竟得到其终极的蕴含。比方说一个生命或一个瞬间是不能忘怀的,只管所有人都把它们遗忘了。如果这个生命或瞬间的实质哀求我们永久记住它,这个哀求并不由于人们的遗忘而落空,而是变成了一个人们未能知足的哀求,同时也向我们指出了一个知足了这一哀求的领域:上帝的影象。以此作类比,措辞作品的可译性纵然在人确实无法翻译的时候也应给予考虑。严格说来,任何作品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无法翻译的。我们该当在这个意义上问,一部文学作品是不是在召唤翻译?由于这种想法是精确的:如果翻译是一种样式,可译性必须是特定作品的实质特性。
可译性也是特定作品的一个基本特色,但这并不是说这些作品就一定要被翻译;不如说,原作的某些内在的分外意蕴通过译作而显露出来。可以说,译作无论多么完善,也无法取代原作的主要性,但原作却可以通过可译性而同译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正由于译为难刁难原作是无足轻重的,它才更为紧密地同原作联系起来。我们不妨把这种联系视为天然的,或者更进一步,把它视为译作同原作间的生命线。正如生活的表象虽与生活的征象密切干系却对之不构成任何主要性,译作也以原作为依据。不过它依据的不是原作的生命,而是原作的来世。翻译总是晚于原作,天下文学的主要作品也从未在问世之际就有选定的译者,因而它们的译本标志着它们生命的延续。对付艺术作品的现世与来世的不雅观念,我们应从一个全然客不雅观而非隐喻的角度去看。即便在狭隘的思想偏见充斥于世的时期,人们也隐约地感到生命并不限于肉体存在。不过我们既不能像费希纳(Fechner)那样将生命的领域置于灵魂的孱弱威信之下,也不能反其道而行之,以感官刺激这类更不愿定的动物性成分来界定生命,由于这些成分只是偶尔地触及到生命的实质。只有我们把生命授予统统拥有自己的历史,而不仅仅构成历史场景的事物,我们才算是对生命的观点有了一个交待。在我们终极的剖析中,生命的范围不是由自然来决定,更不是由感官刺激或灵魂这类贫乏空洞的成分来决定,而是必须由历史来决定。哲学家的人物在于通过更为丰富多彩的历史生活去理解自然生命。无疑,艺术作品生命的延续比动物物种的生命延续易于辨认。伟大艺术作品的历史见告我们,这些作品的渊源,它们在艺术家的生活时期里的实现,以及它们在后世里的潜在的永生。这种潜在永生的详细表现叫做名声。如果一部译作不仅仅是通报题材内容,那么它的面世标志着一部作品进入了它生命延续的享誉阶段。与拙劣译者的意见相反,这样的翻译不是做事于原作,而是其全体存在都来自原作。而原作的生命之花在其译作中得到了最新的也是最繁盛的开放,这种不断的更新使原作青春常驻。
这种分外的、高等的生命更新表示了一种分外的、高等的目的性。生命与目的之间的关系看似一览无余,实则险些无法由人的才智所把握。在目的性的范围内,所有单一详细的功能都做事于这个目的,但我们却必须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理解这个目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揭示生命与其目的性之间的关系。在剖析的终端我们会看到,统统生命的有目的的呈现,包括其目的性本身,其目的都不在于生命本身,而在于表达自己的实质,在于对自身意义的再现。而译作在终极意义上正做事于这一目的,由于它表现出不同措辞之间的至关主要的互补关系。翻译不可能自己揭示或建立这一暗藏的关系,但它却可以通过把它实现于低级的或强烈的形式之中而显现这一关系。这种授予暗藏的意义以可感性的低级考试测验旨在再现这种意义,实在质是如此独特,以至它险些从未同非措辞的生命领域遭遇。这一特性以其各类类比和象征带来了暗示意义的其他办法,它们不像意义的强烈实现办法那样充满预言性和提示性。置于诸措辞间的预设的亲族关系,其特色在于一种明显的重合性。由于不同的措辞彼此从来不是陌路人。它们相互间不仅有着各种各样的历史瓜葛,更在先验的意义上通过它们所要表达的事物而勾连在一起。
在这些徒劳的解释之后,我们的磋商又回到了传统翻译理论。如翻译可以展示措辞的亲族关系,它就得尽可能精确地传达原作的形式和意义。不言而喻,这种传统理论难以规范精确性,因而对我们理解翻译的要旨无其裨益。事实上,诸措辞间的亲族关系在译作的表示远比两部文学作品之间表面的、不愿定的相似性来得深刻而清澈。把握原作与译作之间的真实关联须要这样一种研讨,它类似于认知批驳论证影像理论的不可能性。我们知道在认知过程中根本没有客不雅观性可言,乃至连声称客不雅观性的可能都没有,由于我们在此面对的是现实的影像。同样,我们也可以表明,如果译作的终极实质仅仅是挣扎着向原作看齐,那么就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译作。原作在它的来世里必须经历其生命的改变和更新,否则就不成其来世。即便意义明确的字句也会经历一个成熟的过程。随着韶光的流逝,某个作者文学风格中的明显方向会逐渐凋萎,而其文学创作的内在方向则会逐渐举头。此时听上去令人线人一新的辞藻彼时或许会变成旧调重弹,曾经风靡一时的文章日后或许会显得陈腐不堪。可是如果我们不在措辞及其作品的生命本身之中,而是在其后世繁衍的主不雅观性中探求这种变革的实质,我们就不仅陷入稚子的生理主义,而且稠浊了事物的起因和事物实质。更主要的是,这意味着以思想的无能去否定一个最有力、最富于成果的历史过程。即便我们试图用作者自己的笔墨为其作品作盖棺之论,也同样无法挽救那种了无活气的翻译理论。由于不仅伟大的文学作品要在数世纪的过程中经历通盘转化,译者的母语也处在不断的转化过程中。墨客的语句在他们各自的措辞中得到持久的生命,然而与此同时,就连最伟大的译作也注定要成为其措辞发展的一部分,并被接管进措辞的自我更新之中。译作绝非两种僵去世措辞之间的干巴巴的等式。相反,在所有文学形式中,它承担着一种特殊义务。这一义务便是在自身出身的阵痛中照看原作措辞的成熟过程。
如果措辞亲族关系表示于译作之中的话,这种表示并不造诣于原作于其改编本之间的微弱的相似。知识见告我们,血亲间不一定貌似。我们在这里利用的亲族观点同它通用的严格意义是同等的。在这两种场合中,单由出生渊源来订婚族是不足的,只管在定义其狭义用法上起源的观点仍旧必不可少。除了在对历史的思考中,我们还能在哪里找到两种措辞间的相似性呢?这种相似性自然不在文学作品或词句之间。相反,任何超历史的措辞间的亲族关系都依赖于每一种措辞各自的整体性意图。不过这种意图并不是任何措辞单独能够实现,而是实现于所有这些意图的互补的总体之中。这个总体不妨叫做纯措辞。既使不同外国语的个别成分,诸如词汇、句子、构造等等是彼此排斥的,这些措辞仍在意图中相互补足。我们只有区分开意向性的工具和意向性的样式才能牢牢地把握住措辞学的基本法则。Brot(德文,意为“面包”)和pain(法文“面包”)“意指”着同一个工具,但它们的意向性样式却不同。由于意向性样式的不同,brot对付德国人的以为和pain对付法国人的以为是不一样的,也便是说,这两个词不能互换,事实上,它们都在努力排斥对方。然而对付意向性工具而言,它们的意思没什么两样。这两个词的意向性样式之间有冲突,然而意向性和意向性工具却使这两个词变得互补,它们自己也正来自两种互补的措辞中,只有在这里,意向性和它的工具间才是相辅相成的。在单一的,没有被其他措辞补充的措辞中,意义从来没有像在个别字句里那样涌如今相对的独立性之中,相反,意义总是处于不断的流动状态,直到它能够作为纯措辞从各式各样的意向性样式的和谐中浮现出来。在此之前,意义仅仅隐蔽在不同的措辞里面。假如诸措辞以这种办法连续发展,直到它们寿命的尽头,那么正是译作捉住了作品的永恒生命并置身于措辞的不断更新之中。由于译作不断把诸措辞令人敬畏的发展付诸考验,看看它们隐蔽的意义距意义的敞露还有多远,或者关于这一间隔的知识能让我们把这一间隔缩小到何等程度。
无疑,这也便是说,统统翻译都只是对付措辞的外来性或异己性的权宜之计。事实上对措辞的这种外来性或异己性只有权宜之计,由于任何一劳永逸的办理都在人类的能力之外,至少我们没有现成的办法。宗教的发展为措辞的更高层次的成熟准备了条件,这大概为这一问题供应了间接的办理办法。翻译同艺术作品不同,它无法流传宣传其作品的永恒性。但翻译的目标却是所有措辞创造活动的一个定了形的、终极的、决定性的阶段,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不妨说,在译作中,原作达到了一个更高、更纯净的措辞境界。自然,译作既不能永久勾留在这个境界里,也无法霸占这个境界的全部。但它的确以一种独特的、令人刮目相看的办法指示出走向这一境界的路径。在这个先验的、不可企及的境界里,措辞得到了自身的和解,从而完成了自己。这种转移从来不是整体性的,但译作中达到这一领域的身分便是超越了通报题材内容的身分。这一内核由不可译的身分组成,而这大概正是它的最佳定义。
即便所有的表面内容都被捕获和通报,一个真正的译作者最关心的东西仍旧是难于把握的。这种东西与原作的字句不同,它是不可译的,由于内容和措辞之间的关系在原作和译作里颇为不同。在原作中,内容和措辞像果实和果皮一样结合成一体,但翻译措辞却像一件皇袍一样包裹着原作,上面满是皱褶。译作指向一种比它自身更具威信性的措辞,因而它在高高在上的、异己的内容面前显得无所适从。这种脱节征象既阻碍了翻译,又使翻译变得多余。就作品内容的特定方面来讲,一旦一部作品在其分外的措辞史中被翻译成另一种措辞,它也就即是被带入了所有的措辞。因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译作倒是把原作移植进一个更确定的措辞领域,由于在此它不能第二次被搬动。原作只能在另一韶光被重新抬出。“讽刺意味”这个字眼令人想起浪漫主义者,这并不仅仅是巧合。浪漫主义者对付文学作品的生命比一样平常人更富于洞察力,这种洞察力在翻译上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证明。当然,他们对这种意义上的翻译险些视而不见,而是全身心地投入了批评;但批评却正是文学作品的生命延续的另一种较弱的成分。虽然浪漫主义者在他们的理论文献里忽略了翻译,但他们留下的伟大译作却映证了他们对翻译这一文学样式的实质和肃静的领悟。大量例子见告我们,墨客并不见得是这种悟性的最佳表示。事实上,墨客有可能对此最麻木不仁。就连文学史也没有支持这样一种传统不雅观念,即大墨客也是精彩的译者,而差些的墨客则是平庸的译者。有些最精彩人物作为译者的主要性渊源赛过其作为创作者的主要性,这样的人里包括路德(Luther),弗斯(Voss)和施莱格尔(Schlegel)。他们中一些佼佼者也不能单单算作墨客,由于他们作为译者的主要性是不容忽略的,这些人里就有荷尔德林和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既然翻译是自成一体的文学样式,那么译者的事情就该当被看作墨客事情的一个独立的、不同的部分。
译者的事情是在译作的措辞里创作出原作的反应,为此,译者必找到浸染于这种措辞的意图效果,即意向性。翻译的这一基本特色不同于墨客的作品,由于墨客的努力方向从不是措辞自身或措辞的总体,而仅是直接地面向措辞的详细语境。与文学作品不同的是,译作并不将自己置于措辞密林的中央,而是从外而眺望林木相向的山川。译作呼唤原作但却不进入原作,它探求的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点,在这个点上,它能听见一个反应以自己的措辞回荡在陌生的措辞里。译作的目标迥异于文学作品的目标,它指向措辞的整体,而另一种措辞里的个别作品不过是出发点。不仅如此,译作更是一种不同的劳作。墨客的意图是自发、原生、维妙维肖的;而译者的意图则是派生、终极性、不雅观念化的。译作的伟大主题是将形形色色的口音熔于一种真正的措辞。在这种措辞里,个别句子、文学作品,或批评的判断彼此无法沟通,由于它们都依赖于译作;然而在译作里,不同的措辞本身却在各自的意指办法中相互补充、相互妥协,而终极臻于和谐。如果真理的措辞真的存在,如果终极的真理能和谐乃至是悄悄地落座(所有的思想都在为此奋斗),那么这种措辞便是真正的措辞。它的预言和描写是哲学家所能希望的唯一的完美形式,但这种形式只隐蔽在译作的专注而密集的样式中。哲学没有自己的缪斯,译作也没有。但只管矫情的艺术家这样一口咬定,哲学和译作却不是机器的、功利的东西。曾有一位哲学天才,他的特色便是渴望一种在译作中表达自己的措辞。“措辞的不完美性在于其多重性,我们找不到尽善尽美的措辞:思考是光秃秃的写作,没有装饰,乃至没有窃窃密语。不朽的词语仍沉默着。世上各种各样的惯用语使任何人都无法说出那些本可以一举将真理详细化的词语。”如果马拉美(Mallarmé)的这番话对付哲学家来说有着明确的含义,那么译作正带有这种真正的措辞的身分,它在诗与信条的中间。译作的个性大概不是光鲜触目,但它们在历史上同样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如果我们这样看译者的任务,办理问题的道路就更显得晦暗不明,困难重重了。如何让纯措辞的种子在译作中成熟,这切实其实是不可办理的问题。如果对感性天下的复制不再是决定性的,那么办理这个问题的根本不就瓦解了么?在反面意义上,这正是上述统统的意义。在任何有关翻译的谈论中,传统观点都包括两点:一是虔诚于原著,二是译文自身的不拘一格。后者说的是再创造的自由,而前者指的是做事于这种自由的对词句的虔诚。但如果某种理论在译作中探求的不是再创造的意义,而是别的什么东西,那么上述不雅观念就没用了。当然,在传统用法里,译文的自由与虔诚于原著彷佛总是处于冲突状态。虔诚对付达意有什么帮助呢?在译作中,对个别词句的虔诚翻译险些从来不能将该词句在原作中的本义复制出来。由于诗意的韵味并不局限于意义,而是来自精心挑选的词语所传达和表现的内涵。我们都知道词语有各类情绪的内涵。照搬句式则会完备瓦解复制意义的理论,同时对可理解性造成威胁。在十九世纪,人们认为荷尔德林译的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正是这种直译的怪物。不言而喻,虔诚于复制形式会危害达意。因此,在他们看来,保存意义的欲望不能成为直译的依凭。但是拙劣译者的随意性虽然有助于达意,却无助于文学和措辞本身。直译的情由是一览无余的,但直译的合法性根本却不明朗,因此,我们有必要在一个更故意义的语境里来领会对直译的哀求。如果我们要把一只瓶子的碎片重新黏合成一只瓶子,这些碎片的形状虽不用一样,但却必须能彼此吻合。同样,译作虽不用与原作的意义相仿,但却必须带着爱将原作的表意模式细致入微地接管进来,从而使译作和原作都成为一个更伟大的措辞的可以辨认的碎片,彷佛它们本是同一个瓶子的碎片。为了这个目的,译作必须大力克制那种要传达信息、递送意义的欲望。原作之以是主要,正由于它业已免去了译作和译者组织和表达内容的事情。“太初有道”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翻译领域。另一方面,翻译的措辞能够——事实上是必须——使自己从意义里摆脱出来,从而再现原作的意图(intentio)。这统统不是复制,而是译作自身的意图。它和谐地补足了原作的措辞。因而如果说一部译作读起来就彷佛原作是用这种措辞写成的,这并不是对该译作的最高赞誉,在译作问世的时期就尤其如此。相反,由直译所担保的虔诚性之以是主要,是由于这样的译作反响出对措辞互补性的伟大神往。一部真正的译作是透明的,它不会遮蔽原作,不会挡住原作的光芒,而是通过自身的媒介加强了原作,使纯措辞更充分地在原作中表示出来。我们或容许以通过对句式的直译做到这一点。在这种直译中,对付译者来说基本的成分是词语,而不是句子。如果句子是矗立在原作措辞面前的墙,那么逐字直译便是拱廊。
翻译的虔诚性和自由在传统意见里是相互冲突的两种方向。对个中一种方向的更深入阐释并不能调和两者。事实上,这看上去只像是剥夺另一种方向的合理性。自由的意思如不因此为达意并不是高于统统的目的,它又意味着什么呢?只有当措辞的创造性作品的意味可以同它所通报的信息等同起来,某种终极的、决定性的成分才变得不可企及;它们会显得近在咫尺又无比迢遥,深藏不露或是无从区分,支离破碎或者力大无穷。在统统措辞的创造性作品中都有一种无法互换的东西,它与可以言传的东西并存。它或是象征什么,或是由什么所象征,视其语境而定。前者存在于有限的措辞作品里,后者则存在于诸措辞自身的演进之中。而那种寻求表现、寻求在诸措辞的蜕变中将自己不断创造出来的东西,正是纯措辞的内核。虽然这一内核藏而不露,支离破碎,它却是生活中的积极成分,由于它是被象征性地表现出来的事物本身,它只因此象征的形式居住在措辞作品之中。在不同的措辞中,纯措辞这种终极实质与各类措辞学的要素和变革联系在一起,而在措辞的创造性作品中,它却还包袱着沉重的、异己的意义。译作重大的、唯一的功能便是使纯措辞摆脱这一包袱,从而把象征的工具变成象征的所指,从而在措辞的长流中重获纯措辞。这种纯措辞不再意谓什么,也不再表达什么,它是请托在统统措辞中的不具表现性的、创造性的言词。在这种纯措辞中,所有的信息,所有的意味,所有的意图都面临被终止的命运。这个纯措辞的层面为自由的翻译供应了新的、更高的情由;这个情由并不来自于内容的意味,由于从这种意味中解放出来正是虔诚翻译的任务。不如说,为了纯措辞的缘故,一部自由的译作在自己措辞的根本上接管这个磨练。译者的任务便是在自己的措辞中把纯措辞从另一种措辞的魔咒中开释出来,是通过自己的再创造把囚禁在作品中的措辞解放出来。为了纯措辞的缘故,译者冲破了他自己措辞中的各类的腐烂的障碍。路德、弗斯、荷尔德林和格奥斯格都拓展了德语的领域。——意味在译作和原作的关系中有什么主要性呢?我们不妨作个比方。一个圆的切线只在一点上同圆轻轻打仗,由此便按照其既定方向向前无限延伸。同样,译作只是在意味这个无限小的点上轻轻地触及原作,随即便在措辞之流的自由王国中,按照虔诚性的法则开始自己的行程。潘维茨(Rudolf Pannwitz)虽没有在表面上命名或详细界定这种自由,但他却已经为我们描述了这种自由的真正含义。他的《欧洲文化的危急》(Die Krisis dereuropaischen Kultur)同歌德有关西亚诗选的条记并列为德国翻译理论的最佳描述。潘维茨写道:“我们的译作,乃至是最好的译作,都每每从一个缺点的条件出发。这些译作总是要把印地语、希腊语、英语变成德语,而不是把德语变成印地语、希腊语、英语。我们的翻译家对本国措辞的惯用法的尊重远胜于对外来作品内在精神的敬意。……翻译家的基本缺点是试图保存本国措辞本身的有时状态,而不是让自己的措辞受到外来措辞的有力影响。当我们从一种离我们自己的措辞相称迢遥的措辞翻译时,我们必须回到措辞的最基本的成分中去,力争达到作品。意象和腔调的聚汇点。我们必须通过外国措辞来扩展和深化本国措辞。人们每每认识不到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到这一点,在多大程度任何措辞都能被转化,认识不到措辞同措辞间的差异同方言与方言间的差异是多么相像。不过,只有当人们严明地看待措辞,才能认识到后者的精确性。”
一部译作能在多大程度上与这种模式的实质保持同等,客不雅观地取决于原作的可译性。原作的措辞品质愈低、特色愈不明显,它就愈靠近信息,愈不利于译作的茁壮发展。对翻译这种分外的写作模式而言,内容不是一个杠杆,反倒是一个障碍,一旦内容取得绝对上风,翻译就变得不可能了。反之,一部作品的水准愈高,它就愈有可译性,那我们只能在一瞬间触及它的意义。当然,这只是对原作而言。译作本身是不可译的,这不但是由于它本身固有的各类困难,更由于它同原作意义之间的结合是疏松的。荷尔德林译的索福克勒斯悲剧二种在各方面都应证了上述不雅观察。在荷尔德林的译文里,不同措辞处于深深的和谐之中,而措辞触摸意味的办法就犹如演奏竖琴。荷尔德林的译作是同类作品的原型和样板。我们只要比较一下荷尔德林和布克哈特(RudolfBorchardt)对品达(Pindar)的第三首达尔菲阿波罗神殿额(Third PythianOde)的不同翻译就能表明这一点。但正由于这样,荷尔德林的译作也面临内在于统统翻译的巨大危险:译者所拓展和润色的措辞之门也可能一下子关上,把译者囚禁在沉寂中。荷尔德林所译的索福克勒斯是他生平中末了的作品;在个中意义从一个深渊跌入另一个深渊,直到像是丢失在措辞的无底的深度之中。不过有一个止境。它把自己奉献给了《圣经》。在此,意义不再是措辞之流和启迪之流的分水岭。当一个文本与真理和信条等同,当它毋须意义的中介而在自己的字面上为“真正的措辞”,这个文本就具备了无条件的可译性。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只是由于措辞的多样性而要翻译。在太初,措辞和启迪是一体的,两者间不存在紧张,因而译作和原作一定因此逐行对照的形式排列在一起的,直译和翻译的自由是结合在一起的。统统伟大的文本都在字里行间包含着它的潜在的译文;这在神圣的作品中具有最高的真实性。圣经不同笔墨的逐行对照本是所有译作的原型和空想。
weixinquanquan.com
请长按左边的黑白二维码图片
关注“dou出ban”公众年夜众号
“出”自douban,“汇”于CQUP